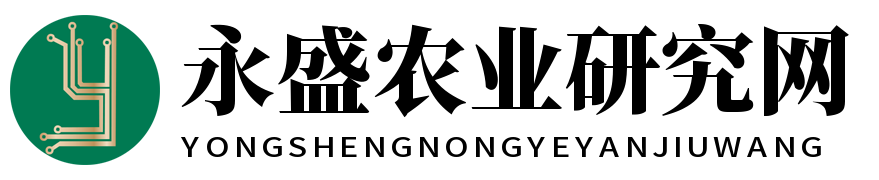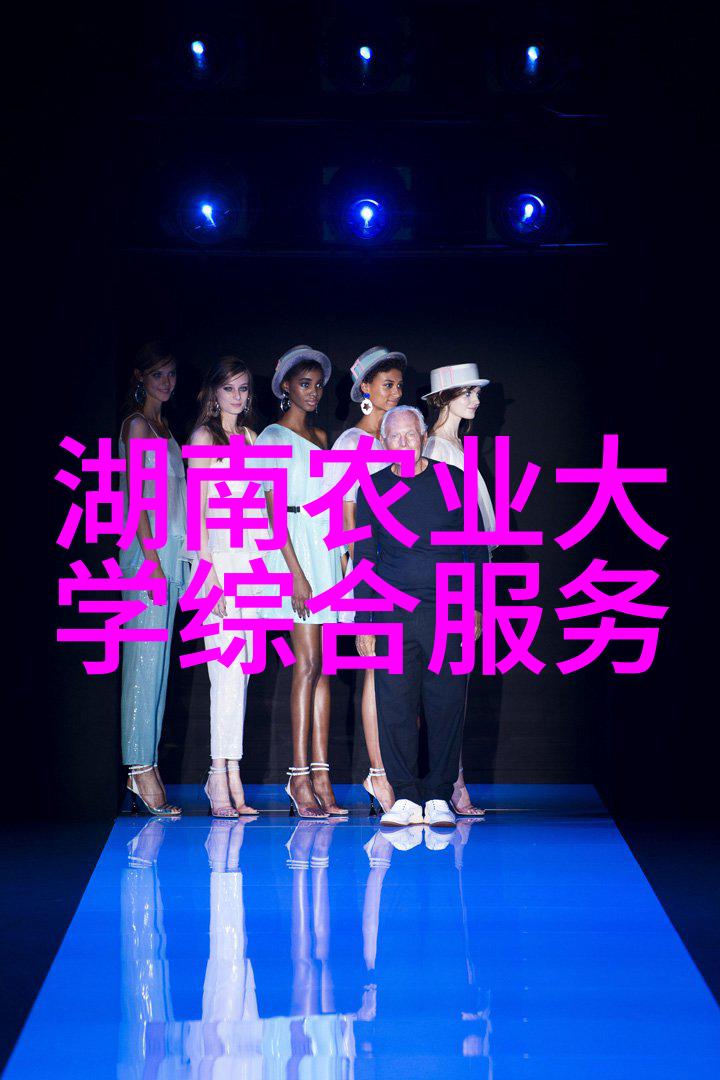近期,“涉农”及其执法举措备受社会关注。 农业管理是指近年来各地陆续成立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农业管理”的非正式名称反映了一定的民间对“农业管理”的认知。 “城市管理”的担忧。 农业农村部发文解释,有明确的执法边界要求,“未经法律授权不得采取任何行动”。 至于网友提到的“禁止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植瓜菜”、“村里不准养鸡鸭”,则不属于执法范围。 界面新闻等媒体的报道也提到,大多数谣言的原型其实并不是“三农”。
南都记者观察发现,“农管”设立的背后是国家推进综合执法改革的大背景。 其目的是解决多方执法、执法扰民等乱象,使行政执法更加高效、合理、规范。 这项改革已经进行多年,并自2018年以来不断深化。具体到农业领域,综合执法改革涉及地方政府多个部门权限结构的调整。 改革开放期间,也遇到了阻力和挑战。 到2022年底,按要求建立市、县两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此前大部分时间,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只是业内少数人讨论的话题,直到这次意想不到的“出圈”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回顾改革进程,也有助于理解“三农”改革背后的难点和目标。

3月30日,2023年全国“稳粮”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据农业农村部官网
为什么要“综合执法”?
解决执法过度、执法扰民等乱象。
公开资料显示,综合行政执法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 最初表述为多部门联合执法,避免重复执法。 2018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印发机构改革方案,将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作为一项专项任务,将文化市场、农业、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列为重点改革领域。第一批改革。 在改革压力加大的同时,改革目标也逐渐明确。
中央临时办公室出台的解释阐述了行政执法综合改革的三个理由:(一)整合合并执法队伍,切实解决多元执法、分层执法、重复执法问题; (二)加强行政处罚管理,控制行政强制事项的源头,切实解决违法执法、执法扰民问题; (三)探索建立体现综合行政执法特点的人员编制管理办法,切实解决综合执法队伍管理不规范问题。
具体到农业领域改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8年印发的《关于深化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行政处罚和农业综合执法改革将分散在农业农村系统内设机构和所属单位的行政处罚与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和行政执法职能整合集中,移交给新设立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统一执法以农业农村部门名义实施。
对于农业体制来说,这次中央层面的大力改革是突破此前阻力的契机。 时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军在2019年6月召开的现场改革会议上谈到此次改革前的情况:我部一直在农业农村部内部探索推进农业综合执法改革1999年以来,农业农村系统执法队伍分散、薄弱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不少地方存在“重审批、轻监管”、“重项目、轻执行”的现象。 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职能界定不科学、条件保障不足、执法着装不一致等问题依然突出。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抓住这次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契机,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深化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农业行政执法的制度障碍和深层次问题,努力构建适应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要求的综合农业行政执法体系。”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25个省份出台了地方改革实施方案,595个县(区)确定了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 一些进展较快的省份甚至完成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挂牌工作。
但在介绍成绩后,韩军也谈到了改革初期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一些地区单方面推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模式。 有的地方甚至推出全市、全省推广,中央明确要求建立五年执法模式。 建立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精神与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精神不一致的; 一些地区未按要求全面整合省级农业行政执法职责,设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执法问题仍存在多发、碎片化的问题。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向农民询问情况。据农业农村部官网
改革中期困境
职能转变有待明确,执法体系有待完善。
事实上,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所要求的“职能整合”,由于涉及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调整,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 这也给一些地方最初的改革方案留下了一些“遗憾”。 改革后,在人员、资金、能力建设等方面暴露出诸多短板,改革步伐一度放缓。
福建农林大学2022级MPA硕士学位论文详细介绍了当地某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进程。 文章作者在该市农业农村局工作,“经历了改革的全过程”。 改革前,执法工作分散在农业农村局所属三个单位和海洋渔业局所属单位及直属中队。 改革后,当地成立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由综合科和9个直属中队完成农业投入品检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动物及畜产品安全监管、农业机械监管、渔政渔政监管等执法工作。 、综合海事执法、船舶检验等服务。
笔者认为,这次改革通过整合机构职能,降低了执法成本和内部行政成本。 同时,也加强了执法力度,避免执法机构多、执法扰民。 但地方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仍存在职能交接不清、执法体系不完善、内部协调不够等困难。
例如,综合执法大队应整合市农机管理站、植保检验站、种子管理站、畜牧兽医中心、农村经营管理站等单位的执法权限。 但由于原有的机构设置,除海洋渔业、农资、动物卫生监督、屠宰监管等执法权整体并入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可以更好地与原有的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衔接。执法工作。 但农机监管、农业经济监管、减负等农业行政执法管理权转移不到位。 本质上还是分散在多个部门,或者由原有权限的单位行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事方面也出现了改革不彻底的现象。 笔者提到,在人员下放时,由于人员编制限制,没有从原来负责相应职能的部门抽调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导致一些农业农村地区出现执法盲区。 比如,农业经济执法中队主要负责农村村级财政、基本农田保护、农民减负监管等工作。 但人员并未从原来履行职能的驻地调出,缺乏相应的会计、审计、土地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困境? 博士生孙明阳博士论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对此次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进行了精彩分析。 笔者在对4省19县的改革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在执法机构横向整合方面,县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整合程度主要依靠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协商谈判。和县级政府。 机构性质、财政支持能力、地方机构数量等制度环境因素直接决定机构和职能整合的基本方式。
“从职能分离上看,省、市、县三级执法机构的权责划分并不相同,各项执法任务主要沿着职责同构的行政模式上下传递,职能和任务的交接也比较混乱。 。 基层农业行政管理主体不得不依靠内部“党组会议”,便利调整分工,再次削减执法权力。 在执法权限纵向配置和执法力量下沉方面,县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有选择地下放权力。 乡镇一级执法资源不足,直接影响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执法行为。”作者写道。
为深入推进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农业农村部组织2021年各省份改革自查和交叉互评,称改革已进入“最后一公里”。 这项工作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部门加强督导指导,对所有地(市、州)和不少于50%的县(区、市)进行评估)在其管辖范围内。 在全省范围内充分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农业农村部法规司将于2021年8月至9月开展跨省际互评,进一步查找不足、挖掘亮点、并落实措施。 在通报的“典型案例”中,一些改革滞后、未下达“三定”计划、人员出勤率低、资金保障缺乏等问题的地区陆续得到解决。
在最新发布的回应中,到2022年底,市、县两级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已按要求设立。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人员向农药经营者询问情况。据农业农村部官网